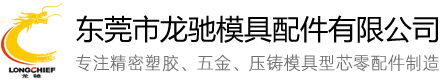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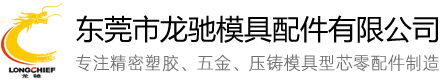
時下,我國經濟運行進入“新常態”,進入由“速度型”向“質量型”轉型升級的關鍵期,其根本特征就是高效率、低成本、可持續。物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之一,國務院印發的《物流業發展中長期規劃(2014—2020年)》明確提出要以提高物流效率、降低物流成本為重點,這不僅是促進物流發展之需,更是提高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率的迫切要求,也是經濟與物流互動發展的基本規律。而要從國民經濟轉型升級的視野來準確把握物流發展規律,必須高度重視統計數據。
一、降低物流成本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
物流成本受到高度關注并非偶然,而是由宏觀經濟發展的根本變化決定的,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經階段。通過統計數據,尤其是基于國際比較的統計數據,我們能夠更準確的把握物流發展的這一個大局。
通過統計數據,把握物流發展規律。發展現代物流是一個國家在轉型升級過程中的必然趨勢,具有一定的規律性。轉型升級最核心的內涵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,實現經濟發展由“速度型”向“質量型”轉變,其根本的特征就是高效率、低成本、可持續。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尤其是美國上世紀70、80年代的發展經驗表明,物流是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的突破口。根本原因在于,物流不局限于某個行業或者某個領域,而是貫穿于生產、流通和消費各個環節,貫穿到整個社會經濟的全過程。物流不僅服務于生產制造,也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,尤其是在電子商務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更是如此。也就是說,現代物流的優化發展,提高的是整個經濟運行的效率,降低的是整個供應鏈的運行成本。
通過統計數據,把握物流發展基本格局。基于國際比較的物流統計數據表明,2014年,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為16.6%,盡管有所下降,但仍高于美國、日本一倍左右,而且高于巴西、印度等發展中國家,相當于美國上世紀80年代初的水平。當前,在勞動力成本、能源資源成本剛性上漲的背景下,降低物流成本是最有效的途徑,具有緊迫性,而且潛力巨大。
|
區域
|
國家
|
2012年GDP
(十億美元)
|
2012物流費用
(十億美元)
|
物流費用與GDP比率(%)
|
|
北美
|
加拿大
|
1819.0
|
163.7
|
9.0
|
|
美國
|
15680.0
|
1334.6
|
8.5
|
|
|
歐洲
|
法國
|
2609.0
|
247.6
|
9.5
|
|
德國
|
3401.0
|
299.7
|
8.8
|
|
|
亞洲太平洋
|
中國
|
8227.0
|
1480.9
|
18.0
|
|
印度
|
1825.0
|
237.1
|
13.0
|
|
|
日本
|
5964.0
|
506.9
|
8.5
|
|
|
韓國
|
1156.0
|
103.9
|
9.0
|
|
|
南美
|
阿根廷
|
475.0
|
57.0
|
12.0
|
|
巴西
|
2396.0
|
277.9
|
11.6
|
|
|
全球
|
71830.0
|
8350.6
|
11.6
|
|
如果放到全球背景下來把握我國物流發展大局,尤其是從發達國家的物流成本核算歷程來看,我們的認識會更加清晰。
宏觀物流成本核算起源于美國,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60年代初。1962年,美國哈佛大學Heskett J.L.教授提出了較系統地宏觀物流成本(Macroeconomic logistics costs)核算方法,并逐漸成為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南非等世界各國通用的方法,我國的物流統計核算也采用此方法。宏觀物流成本具體包括運輸成本、存貨持有成本、物流管理成本。1973年,美國Cass信息系統公司開始計算美國的宏觀物流成本,現在每年將研究成果發布在《美國物流年度報告》上。1980年,美國宏觀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為17.2%,位于較高水平,如表2所示。
|
年份
|
宏觀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
|
年份
|
宏觀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
|
年份
|
宏觀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
|
|
1980
|
17.2
|
1991
|
10.6
|
2002
|
8.8
|
|
1981
|
16.2
|
1992
|
10.0
|
2003
|
8.7
|
|
1982
|
14.5
|
1993
|
9.9
|
2004
|
8.8
|
|
1983
|
13.3
|
1994
|
10.1
|
2005
|
9.4
|
|
1984
|
13.4
|
1995
|
10.4
|
2006
|
9.8
|
|
1985
|
12.4
|
1996
|
10.2
|
2007
|
9.9
|
|
1986
|
11.6
|
1997
|
10.2
|
2008
|
9.3
|
|
1987
|
11.4
|
1998
|
10.1
|
2009
|
7.8
|
|
1988
|
11.5
|
1999
|
9.9
|
2010
|
8.2
|
|
1989
|
11.7
|
2000
|
10.2
|
2011
|
8.5
|
|
1990
|
11.4
|
2001
|
9.5
|
2012
|
8.5
|
為什么宏觀物流成本核算誕生于上世紀60、70年代呢?主要是因為當時的宏觀經濟背景發生了根本性變化。60年代末、70年代年初,美國等發達國家逐漸由“快速發展”進入到“滯漲階段”,經濟增速下滑、鋼鐵市場飽和、一些產品出現過剩;加上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導致世界石油危機爆發,油價暴漲,從1973年年底到1974年年初,原油價格在短期內從每桶3美元漲到了12美元,此后高位運行,大幅推高了經濟社會的運行成本。
在這樣的背景下,“成本高、效益低”的問題水落石出。然而,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益的出路在哪里呢?在各項成本中,能源成本高位運行、勞動力成本具有剛性,根據物流統計數據發現,降低物流成本有巨大潛力,最終以降低物流成本為突破口,通過優化業務流程,進而降低整個經濟社會運行成本。同一時期,在日本,通過物流發展來降低經濟運行成本的“第三利潤源”學說逐步興盛。也是在這一大背景下,物流成本核算應運而生,逐漸由理論走向實際,以確切地衡量一國的物流成本,指導物流發展政策;宏觀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也逐漸成為國際比較中的一個核心指標。
美國、日本的發展經驗表明,降低物流成本是經濟轉型升級的必經階段,需要引起高度重視。相比較而言,我國的情況與當時的美國頗為相似。為此,發展現代物流是宏觀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,而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。
二、我國將進入物流成本回落期
我國經濟運行中的物流成本偏高已成為共識,但根據統計數據可以發現,物流成本變化具有內在的客觀規律,與一國的經濟發展進程相一致,不能脫離宏觀經濟的發展水平孤立地看待成本偏高的問題。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,物流成本由高到低變化一般需要經歷四個歷史時期。
短缺經濟時期,物流成本處于上升階段。在短缺經濟時代,經濟主體能夠通過規模擴張獲取增量收益,成本問題并沒有受到高度重視,經濟發展方式以粗放的外延擴張模式為主。物流發展的主要目標不是降低成本,而是幫助工商企業擴大銷售規模,在這一階段,物流成本不斷上升。同時,短缺經濟階段通常是第二產業占比不斷提高的階段,在工業化進程快速推進的過程中,物流需求規模加快增長,物流成本也必然不斷上升。在美國,上世紀60、70年代以前,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也高達17%以上。在我國,上世紀90年代初,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高達24%。
過剩經濟階段,物流成本變化進入平臺期。隨著經濟發展由短缺經濟進入到過剩經濟階段,而在經濟結構沒有發生實質性轉變的背景下,物流成本由“快速上升期”逐漸過渡到“高位平臺期”。2000以來,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有所下降,但下降緩慢,尤其是在近幾年產能過剩矛盾較為突出的階段,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進入一個平臺期,該比率一直保持在18%左右。
經濟轉型時期,物流成本快速下降。在過剩經濟背景下,產能過剩導致供需矛盾凸顯,“高成本、低效率”的問題水落石出,在這樣的背景下,一方面,推進經濟結構調整、化解產能過剩成為必然選擇,物流規模增速回落;另一方面,經濟發展由速度型轉變為質量型,其核心問題是提高效率、降低成本,由于物流業滲透到國民經濟各領域,在各方面降低成本的壓力下,物流成為降本增效最有效的方法,此時,物流成本會出現快速下降。以美國為例,上世紀80年代以來,美國以信息技術為核心和支撐,大力調整產業結構、發展第三產業,物流成本水平進入下降階段,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降低了將7個多百分點。
經濟轉型過后,物流成本保持在較低水平。近年來,美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穩定在70%以上,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也穩定在9%左右,保持在較低的水平。
過去近10年,我國處于經濟全面過剩時期,物流成本位于高位平臺期,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沒有太大變化是正常現象,而現在,經濟社會正經歷著從過剩期向轉型期的發展,我國的物流成本也正在由“高位平臺期”向“快速回落期”轉變。2014年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有所下降,一方面是受貨運量、貨運周轉量及GDP數據調整的影響,另一方面也是我國經濟結構變化的結果,是物流成本變化規律的體現。
三、2020年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有望降至15%以內
物流成本變化的內在規律表明,降低物流成本的關鍵就是要調整經濟結構。從我國物流市場結構來看,工業品物流占主導地位,占全社會物流總額的92%左右。2014年,社會物流總費用為10.6萬億元,按照工業品物流總額所占的比例初步估算,花費在工業品物流上的物流成本在9.7萬億元左右。所以說,提高工業品物流的效率、降低工業物流的成本至關重要,是重點領域。
與之相應,從經濟結構來看,相對而言,第二產業對物流的需求規模大于第三產業,物流成本耗費也高于第三產業。因而,降低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,換句話說,大力發展第三產業,能夠有效降低物流成本。
根據美國的歷史數據進行分析表明,在美國,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每上升1個百分點,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下降約0.6個百分點。
.gif)
數據來源:《美國物流年度報告》、《中國統計年鑒》。
圖1:美國產業結構變化與物流成本的走勢變化 單位:%
從我們的統計數據來看,通過經濟結構調整來降低物流成本的效果也十分明顯。從1991年到2014年,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每上升1個百分點,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下降0.5個百分點左右。
.gif)
數據來源:《中國統計年鑒》、中國物流信息中心。
圖2:中國產業結構變化與物流成本的走勢變化 單位:%
近幾年,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年均上升1個百分點左右,隨著城鎮化進程的加快、產業結構調整力度加大,初步預計,2020年,第二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將下降6個百分點左右,與之相應,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將達到53%左右,較目前上升6到7個百分點。
由此預計,按照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每上升1個百分點,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下降0.5個百分點計算,到2020年,我國社會物流總費用與GDP的比率將下降至14.5%左右。
四、從更長期來看,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將保持在10%左右的較合理水平
在當前及未來相當長時間內,降低物流成本是真正有效的“第三利潤”源泉,是提質增效的抓手。然而,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不是越低越好,而是有一個合理的低位水平,現代經濟要高效穩定運行,必須要付出一定的物流成本。縱觀世界物流轉型升級歷程,這也是物流發展過程中的必然規律。
實物配送階段,物流成本高位運行。從產業發展歷程來看,制造業和現代物流發展一直是互動的,密不可分的。當生產方式處于“少品種、大批量、流水線生產模式”的時候,物流發展處于實物配送階段(Physical Distribution,PD),物流功能單一,物流信息化、一體化程度較低,物流在生產流通中處于從屬地位,其功能只是為生產流通企業擴大銷售規模。在這一階段,物流成本水平處于高位運行階段。在美國,上世紀60、70年代以前,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也高達17%以上。
一體化物流階段,物流成本不斷下降。當生產規模擴張達到一定的程度,產品出現過剩、各項成本上升,不計成本的“大批量”生產方式難以為繼,轉而通過發展現代物流,保障產業流程優化、供應鏈構建,進而獲得成本降低的效益,物流在生產流通中的地位也不斷上升,成為企業優化資源配置、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。上世紀80年代以來,美國的制造業生產方式逐步由傳統的“少品種、大批量”向“柔性化敏捷制造” 模式轉變,加上美國打造“信息高速公路”,由此推動物流發展由“實物配送”向“一體化物流”階段(Logistics)發展,物流信息化、一體化快速發展。這一階段,物流發展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效率,幫助工商企業降低成本。在美國,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由17%以上降至2001年的10%以下,共經歷了20多年時間。
供應鏈階段,物流成本低位波動。在后工業化時期,供應鏈模式(Supply Chain Management,SCM)廣泛運用,物流專業化、精細化運行,在這一階段,物流上升到戰略管理的主導地位,通過去除冗余物流環節和物流過程,最大限度的高效集約利用物流資源,促使物流成本在較低的水平上波動變化。近10年來,美國的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一直在9%左右波動,日本的這一比率在8.5%左右波動。
從物流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,物流成本并不是無限下降的,而是有一個下限,這個下限正是物流集約高效運行的結果。目前,我國物流發展正處于由“實物配送”向“一體化物流”發展的階段。可以預計,隨著物流方式的轉型升級,當我國物流發展到供應鏈階段,同時,第三產業比重上升到60%左右,物流成本與GDP的比率將保持在10%左右的較合理水平。
總而言之,通過統計數據,我們深刻地認識到,發展物流的目標和方向十分明確,就是提高社會經濟運行的效率,降低全社會的物流成本。同時,要緊密結合宏觀經濟環境和物流轉型升級歷程,準確把握物流成本的變化規律。
基于此,降低物流成本需要多措并舉,一是堅定不移調整經濟結構,大力發展服務業;二是進行物流管理方式的升級,推動供應鏈的發展;三是政府要簡政放權降低行政性收費,形成較好的物流發展環境;四是與時俱進做好物流統計工作,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不斷完善物流成本核算體系,更好地把握物流成本變化規律。